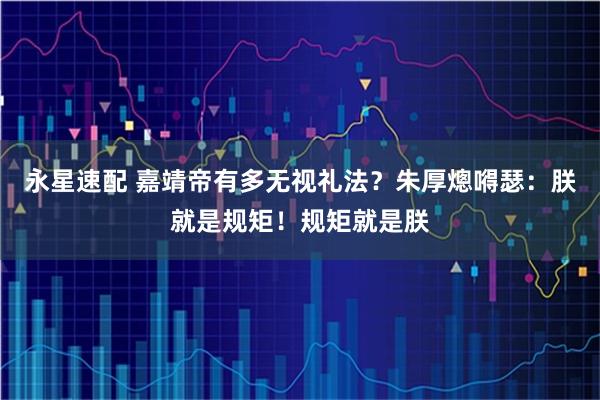
文|星海永星速配
编辑|星海
文|星海
编辑|星海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
嘉靖元年,紫禁城内,气氛冷冽。年仅十五岁的新君朱厚熜登上皇位,不曾阅兵,不曾校场,第一场战斗就在纸面上打响。他不肯认“孝宗”为父,也不接受“冒名”的太庙祀典。
他提出的要求看似简单——生父应尊为皇帝,生母应称皇太后。这话一出口,满朝震惊。群臣劝,他不听。劝多了,他动手。一场关乎“礼法”与“皇权”的角力,就此爆发。
即位之后,风起太庙
嘉靖元年,四月二十日,明武宗朱厚照驾崩。宫中哀乐未停,继承人问题立刻摆上案头。皇室无嗣,京中权臣商议继立远支。内阁首辅杨廷和提议迎立兴献王之子朱厚熜。朱厚熜时年十五,尚在湖北安陆。
展开剩余90%文书下达,官员前往安陆迎驾。朱厚熜接受旨意,进京即位。他是皇帝,却不是正统皇子。名义上,是“兄终弟及”;礼法上,是“继统非出”。他明白自己身份特殊,也明白这身份带来的礼法裂缝。他没声张,但没有一件事他不记在心里。
五月初一,奉天殿登基大典。礼仪如制,文臣百官行三跪九叩之礼。朱厚熜目视台下,神色平静,动作简洁。他接过玉玺,口称“承祖宗大统”,却不提孝宗一句。接下来的日子,他开始处理政务。朝中群臣上表恭贺,新皇即位,祀典未定,必先定“皇考”称谓。
这才是第一根刺。
群臣按照祖例,起草奏章,称孝宗为“皇考”,朱厚熜为“嗣皇子”,强调“承先统”。一纸文字,激怒新帝。他批得极快,写:“朕生于兴献王府,何得称孝宗为父?”没人想到,他会直接推翻宗法起点。
礼部尚书毛纪最先反应。他找杨廷和密谈,认为新帝年幼,应暂缓祀典争议。但朱厚熜接连召见张璁、桂萼等年轻士人,态度坚决。张璁建议:追尊生父为帝,可入太庙,名为“睿宗”,理可通变。这成为一场礼制风暴的发令枪。
嘉靖元年六月,第一次朝会讨论“皇考归属”。毛纪明确反对,称“既为嗣子,当奉宗父”。朱厚熜脸色未变,只问:“何法可据?”毛纪引《大明会典》《明太祖谥法》,历引三朝成例。朱厚熜点头,未再争。朝臣退后,他却在私下召见张璁,命其草拟“尊父为帝”诏书草案。
七月,诏书草案完成。内容明确提出“兴献王当追谥为帝”,神主拟称“睿宗裕皇帝”,祀入太庙第三列,次于太祖、成祖。桂萼负责庙制设计。两人迅速行动,未经礼部审议,绕过毛纪,递入内廷。
毛纪震怒,上书谏阻。朱厚熜未回,只是把奏折交张璁批注,再递回给事中。朝中议论四起,多位官员加入谏言。王元正、李梦阳、乔宇等人提出“不可祀非统宗”。他们坚持,生父非正统血脉,不能擅祀。
朱厚熜开始动手。他命锦衣卫监控反对大臣动向,密令外放毛纪,令其“巡抚南直隶”,实则软禁。杨廷和告病归里,礼部诸官换血。没有流血,但政局已翻盘。
九月,第二道诏书下达。命工部选地,建世庙。地址在皇城东南,规格比照太祖庙制。百官面色如土,唯张璁、桂萼跪谢圣恩。御史齐继宗上疏称:“祀典动根本,臣窃惧。”朱厚熜直接命其入狱问罪,廷杖二十,贬为庶人。他不再藏锋,开始逐一清算。
同年冬,世庙动工,神主木雕已制。嘉靖帝亲自定制神主铭文,谥号、庙号、位列,逐一确认。他避开群臣,召见亲信,日夜核定庙规。张璁进言调整祀日,他准。桂萼提出以“皇子礼”兼顾“继嗣礼”,他斥:“无此二义,唯朕所定。”
大礼议起,臣下失势
嘉靖二年春,张璁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。权柄骤升,引起朝中不满。桂萼则被任为翰林院修撰,专责修改会典中相关祀典章节。两人形成嘉靖礼制改革核心。毛纪旧部、杨廷和门人多有上疏反对,但均被压制。
最激烈的,是在御史屠滽的奏折中。屠滽直言:“尊生父为帝,是乱昭穆,废宗统。”他被廷杖四十,贬为潮州判官,途中病死。这是大礼议中首位“折命之臣”。
嘉靖不以为意。神主已经立起,庙已封顶。他开始要求太庙祀典调整。原顺序为太祖、成祖、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。嘉靖提出:“应列睿宗于第三位,其后再序历朝。”礼官反复请示,答复永远是一个字:“准。”
礼部侍郎顾璘私下请张璁斡旋,被弹劾“结党营私”,贬至南昌。张璁提议修撰《睿宗实录》,由桂萼执笔,三个月成书。内容包括睿宗“训子有方”“民间贤王”等事,虽无记载,却无人敢提异议。史料成为嘉靖意志的延伸。
嘉靖三年春,张璁入内阁,权重一时。他着手修改《大明会典》,彻底将“睿宗”列入太庙祀典法条。原文“列历代皇帝位次”部分被删除,新增“凡皇帝生父,若追尊为帝,应立世庙,祀如制”。这一条款,经中书舍人四审,未改一字。
百官明知不合祖制,却无一人敢抗。此前有反对者不是被打就是被贬,朝中气氛日趋压抑。议礼之声逐渐熄灭,大礼议已由纸上争论,变成现实格局。
同年冬,世庙举行初次献祭,嘉靖身穿吉服,亲自行礼。礼官规避多处争议,使用模糊术语,如“皇亲”、“献帝”。嘉靖当场修改祝文,加上“朕之父睿宗”字句,礼官低头无言。
祀典结束,他回乾清宫,未言一字。张璁、桂萼随侍,呈上神主定本。嘉靖亲笔在其下写:“此位永定。”
这一笔,意味着祖制已改。谁再议礼,便是抗旨。
分祀天地,庙制重构
嘉靖三年之后,朝中反对声音大幅减弱。御史不言,礼部谨慎,内阁顺从。张璁、桂萼地位巩固,世庙正式列入国家祀典。但嘉靖并未止步。他将目光投向更广——天地祀典。
他认为天地合祀不合古礼。《周礼》记“天地异坛”,《礼记》称“日祭于朝,月祭于夕”。嘉靖引用古籍,指出自太祖以来合祀天地不合“上古之法”。他说应分坛、分地、分祀,不可混淆。张璁附议,建议在京师另设“地坛”“日坛”“月坛”。
嘉靖五年初春,命工部定址。地坛在北城,月坛在西,日坛在东,按《礼记》星宿方位布置。他亲自圈地,命太监监工。三月动工,六月完工。朱漆丹柱,青砖素顶,四坛皆建。建成之日,未奏凯歌,仅留旨意两行:“依古礼建坛。朝祭有常。”
群臣虽感突兀,却无力劝阻。桂萼撰《坛典新仪》,规定祭天地、日月各以四时举行,皇帝亲祭,百官陪祀。原本每年冬至合祭天地的郊祀仪式,拆分为两场。冬祭地坛,夏祭天坛;春祭日,秋祭月。时间地点、供品服色,皆按嘉靖设定执行。
礼部曾建议由官代祭,以减频繁动驾之劳。嘉靖拒绝。他亲自乘辇出宫,每年四次,按坛就位。神乐声中,朱袍映坛,内监递圭。臣工跪伏,不敢仰视。从未有皇帝如此执着亲祭,从未有礼制改动如此彻底。
他命内阁修改《郊祀录》,增列“天坛”“地坛”“日坛”“月坛”各项仪节。张璁重新校订祷文,凡提“上帝”者皆改为“皇天”;凡称“天命”者删去,以“感灵”“致诚”代替。他要求所有祝文不得有“奉先帝制礼”,只书“奉圣训”。
这一系列动作,改变的不只是祀典制度,更是朝廷书写权力的方式。原本由祖宗立的礼法,变成皇帝手里的工具。
嘉靖六年秋,九庙重修。他认为太庙列序不清,睿宗庙制规格未足。命工部拆除东配殿,增建三殿,并列太祖、成祖、睿宗。三位帝王庙门等高,门额同宽,殿柱等长。工部尚书反复建议“高低应异”,他批:“改。”
建筑完工,礼部定昭穆。嘉靖再度亲自改定,命睿宗列第三位,孝宗、武宗之后。礼部尚书徐阶私下与张璁议:此举违制,恐留话柄。张璁答:“君意已决。”徐阶沉默。无文臣再提异议,所有规矩已被改写。
嘉靖亲自巡视新庙,命书“睿宗裕皇帝神位”金匾,挂于大殿中。门口守卫两班,轮值昼夜。太庙之外,唯此庙有此待遇。庙前设仪门、丹墀、乐舞台,皆仿太祖庙制。国子监礼生每日早课,需在此庙祭读章文。
他还设“世庙志”,由桂萼主编。共十卷,记述睿宗事迹、祀典经过、庙制沿革,全部采信嘉靖口述,不采地方志。张璁称其为“正统立传”,朱厚熜批:“可。”
他没有改变朝代,却重设朝代的记忆方式
规矩书成,谁敢再言?
嘉靖八年,世庙首次“祔正典礼”举行。日未出,钟鼓先响。大殿香烟缭绕,宫中百官列队至庙前。朱厚熜身着大祭服,步履缓慢登阶,身后桂萼执帛书,张璁持圭器。
祭典开始,太常寺官念祝,读至“皇父睿宗”处时,声音微颤。殿中寂静。嘉靖未言,望神位而拜,三拜九叩,起身,转身离去。整个典礼,仅用一刻,无言之下,全朝皆服。
此后,祀典按新制年年举行,无一人再议“宗统”、“冒父”之说。旧臣死者如毛纪、屠滽,贬者如乔宇、顾璘,皆无复职。新臣皆出张璁门下,称礼为“圣训”,称庙为“新制”,无人再提“祖宗定礼”。
嘉靖九年,桂萼奉旨修《明礼通典》,将新建祀典、世庙祭祀、天地四坛、神主位序全部录入,合五十卷,装帧金线,列于内阁档案。《明实录》亦据此修订,删去早年礼争记录,只记“皇帝定典,尊父祀之”。
张璁离世后,徐阶入阁。徐阶谨慎应对,所有事皆请示,不敢擅断。嘉靖倦政,常年居乾清宫不出,朝会稀少,政务批红简短。除祭祀之外,不临朝三月为常。
他把规矩写进了制度,也写进了“沉默”。群臣不敢多言,制度无人敢改。所有《大明律》中有关“宗法祀典”之条,皆未再动。他自己说过:“书成,则礼定。”他信这句话,也信只有由他落笔,才有资格称为“礼”。
乾清宫的卷帘常闭,宫门上朱红未退。皇帝已不多出,但他的制度四处可见。官员行祭、学生讲礼、礼部颁典,处处引用嘉靖年间制度。即使后世皇帝尝试变更,也往往“参嘉靖旧制”。
至此,“朕就是规矩,规矩就是朕”虽非出自其口,却实实刻于明制之中
没有公开对抗,没有刀兵动乱永星速配,仅靠一人之志,一纸一诏,便将祖宗制度尽数更易。明人不议,后人默记。
发布于:北京市51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